北平和平解放前,最后一篇得以保存的以九三学社名义发表的文献
全文约5600字 | 阅读需12分钟
收录于《自由文丛》里的《九三学社对时局的几点意见》 《意见》全文如下: 九三学社对时局的几点意见(来件) 一,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全国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今日夜所企求之和平非但无望,而总动员令又复颁发。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对外长期战争中,消耗已尽,若再因内战而全面动员,直等于以国命作孤注之一掷。同人等为保持国脉民命起见,对政府此举认为遗憾。 二,中国为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人民与党派,对于国事,自有其自由发表意见之权利,无论其与政府党派所施行之政策,违背与否,不得干涉。同人等因此,对国府副主席孙科七月七日在上海对记者谈话中,有云:“动员令颁布,反对内战等于反对国策,亦即反对政府,当然要取缔,不容其存在”之语,认为有违反民主国家之立国精神,侵犯人民权利,深属不当。 三,在对外抗战期中,美国给予我们的援助,中国人民至深感激。胜利后虽有助长与鼓励中国内战之种种行为,然人民仍望其能有所改正。今复变本加厉,公然出售军火弹药一万三千余万发之多,此无异直接屠杀中国人民,为民族生存之起见,对于美国政府此举,提出抗议。 九三学社三十六年七月八日 《意见》结尾的日期为1947年7月8日。刊登《意见》的刊物名为《沧南行》,原书目录上写着“自由文丛社发行 香港天后庙道金龙台三号”,没有出版日期。经查找相关资料发现,《自由文丛》1947年6月创刊于北平,主编为吴晗。 吴晗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委。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当局对此十分恐惧和仇视,采取种种手段扼杀一切进步活动。吴晗回忆说,“到一九四七年,许多刊物都被查封了,我们只好出地下刊物,一期换一个名目,一共出过三本,记得一期叫《社会贤达考》,一期叫《论南北朝》,还有一期连名字也想不起来了。我们好容易弄到一点钱,凑着出一期,谁知发到东安市场、西单商场书摊以后,尽管卖光了,但是钱却收不回来,我们也不敢要,只好另外想办法再出一期……”吴晗想不起名称的这一期地下刊物,正是《沧南行》,为《自由文丛》第2期,名称取自刊物中一篇较长的同名通讯报告。其发行地址“香港天后庙道金龙台三号”,并非真实信息。据张友仁回忆,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书上有的印着香港出版,有的印着上海出版的字样”。 《沧南行》在内容上以抨击时政、要求民主为主。除了刊有《意见》外,封里印有闻一多先生遗像二帧,收录有关时局的短评、论文、杂文、通讯报告16篇,包括闻家泗等的三篇纪念闻一多死难一周年的文章,张奚若谈时局的访问记一篇,马叙伦的诗二首等。 《意见》既不见于九三学社中央社史办公室所编《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所编《九三学社》,也未见于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所留存的档案资料。它的发现,为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九三学社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提供了新资料,充实了新内容,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意见》第一条,对国民党政府颁布总动员令的举动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对外长期战争中,消耗已尽,若再因内战而全面动员,直等于以国命作孤注之一掷”。1946年6月26日,在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全面内战之初,九三学社就发表《对时局意见》,明确提出,“人民困苦以极,亟需休养生息,任何党派军队,倘为人民着想,就应立即放下屠刀,实行全面永久停战,静候和平调处。”9月3日,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周年之际,九三学社发表《为国际胜利周年纪念宣言》,主张“国、共双方应立即全面停战,停止一切破坏工作,实行《政协决议》,改组政府。”10月2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其他各方代表重返南京,恢复国共和平谈判,蒋介石竟飞赴台湾,顽固拒绝和谈。九三学社于10月24日发表《对时局六点意见》,斥责国民党蒋介石“有使全国人民及世界人士怀疑政府对和平谈判之诚意”。为使其统治披上合法外衣,国民党于11月至12月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在此前后多次发表呼吁书、谈话和宣言,予以坚决反对和抵制。 1947年,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主动权开始转移到共产党人的手中。7月4日,为解决国民政府军事、政治上的危机,蒋介石颁布“戡乱”总动员令,实行“戡乱救国”,加紧对国统区人民的掠夺和镇压,企图集中全力与中共一搏。在九三学社看来,这一举动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再次发表《意见》,强调“为保持国脉民命起见,对政府此举认为遗憾”。由于社员大都身处国统区,《意见》在用词上是较为克制的,但仍然充分表明了九三学社在国共两党斗争中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即坚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 《意见》第二条,对孙科有关“总动员令”的谈话进行了直接批评,强调“民主国家的人民与党派,对于国事,自有其自由发表意见之权利”,认为谈话“有违反民主国家之立国精神,侵犯人民权利,深属不当”。崇尚民主、追求民主是九三学社的政治理想和重要政治主张。九三学社的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名称中即含有“民主”二字。自创建以后,九三学社一直在为推动民主而鼓与呼。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发表《成立宣言》强调:“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1947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发表《纪念“五四”宣言》,指出,“我们深信,挽救目前中国,要在实行民主,努力科学……从民主的团结,救人民于水火,否则一切都谈不到。”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始终坚持反人民的独裁专制,根本不理会这些呼吁民主的声音。这些明显违背民主原则的言论,不能不使九三学社对国民党彻底失望,进而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走上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 《意见》第三条,对美国政府帮助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的行为,提出了严正抗议。中国全面内战爆发之初,美国以“友邦”身份介入,在国共两党之间实行所谓的“调停”,实质上却是企图通过扶植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削弱以苏共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力量,为日后称霸世界奠定基础。一开始,九三学社对马歇尔的“调停”还寄予一定希望。在1946年5月4日发表的《对时局主张》中,九三学社指出,“请马歇尔元帅彻底实行调人责任,对两党争执,予以仲裁,立即实行全面调停。”同时希望“在中国政府未根据政协协议改组以前,美国政府勿予中国任何一党派以任何援助(包括借款及运输军队)”。随着内战的激烈进行,九三学社的前辈们发现,美国不仅没有尽到“调停”责任,反而“继续作军事援助,殊有近于偏袒之嫌疑”,由此开始转变对美态度,一方面明确反对“外国在华驻军权、内河航行权”,另一方面则要求“在华美军应即撤尽”“采取公正的公立的态度,帮助中国人民制止内战”“否则中国人民认为马歇尔特使,亦如驻华美军一样无继续留华之必要”。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暴行,激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愤怒。许德珩、袁翰青等九三同人同北京大学48名教授发表《为沈崇事件致司徒雷登大使抗议书》,抗议美军暴行。后又于1947年1月20日以九三学社留平同人名义发表《时局意见》,强调“国际关系应本独立自主的立场,平衡发展,反对一面倒的半殖民地的作法。”继而至1947年7月,九三学社发表《意见》,再度痛斥美国的援蒋政策,强调“今复变本加厉,公然出售军火弹药一万三千余万发之多,此无异直接屠杀中国人民”。这也标志着九三学社彻底认清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真正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在此之后,九三学社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系列斗争,比如“反美扶日”运动、批判美国政府白皮书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创建到北平和平解放,九三学社一直关注着时局,散布在北平、上海、重庆、南京等地的社员经常在本地集会,研究工作开展。例如,从1946年冬至1947年5月,九三学社在北平的社员,“集会座谈,不下十次,几于每半月即举行一次,籍以交换意见,并检讨国内外情势。”每到时局关键时刻,九三学社都会“有所表示”,“力促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声援政协各代表完成历史任务。对当时的各项问题如:政权的开放;民主与自由权利的保障;军事冲突的停止;保甲制度的废除;及严惩汉奸释放政治犯等问题,均曾提出严正的意见”。 1947年是中国革命和解放战争的转折之年。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稳定后方,在其统治区内极力加强特务活动,迫害和镇压爱国民主力量。在7月颁布“总动员令”后,国民党当局又于8月中旬训令特务组织,对民主党派上层分子“暂时容忍敷衍”,对其中下层分子则不必客气,只要发现,不问其情由如何,“一律格杀勿论”。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严加取缔”,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意见》正是九三学社在这样一个关键和特殊时期,针对国民党当局颁布“总动员令”、孙科谈话以及美国援蒋政策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献。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何九三学社创始人和相关档案资料均未直接提及这篇文献?笔者认为,这与刊登《意见》的《沧南行》是一本地下刊物且可能的知情者去世较早有很大关系。《意见》标题后面有“来件”二字,意为送来或寄来的文件。谁送来或寄来的呢?很可能是九三学社创始人、常务理事张雪岩。原因有二:其一,张雪岩是出版《自由文丛》的重要支持者。据柯灵回忆,“民盟张雪岩从美国回来,愿出资兴办刊物,鼓吹民主,吴晗找了静远,静远又找了佘世光,合办《自由文丛》。刊物不履行登记手续,不公开编者与出版人,在各大学秘密流通。”其二,《沧南行》中同时收有张雪岩一篇名为《社会学与政治》的文章,该文从探讨社会学与政治的关系着手,表达了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因此,《意见》发表在《沧南行》上,很可能与张雪岩的推荐有关。当然,许德珩等九三学社创始人与吴晗经常在一起“搞活动”,也不能完全排除是许德珩等人把《意见》交给吴晗发表。正如九三学社创始人袁翰青回忆:“当时,有组织的民主人士在北平的不太多,并没有把各民主党派分得那么清,常常是配合在一起搞活动的……我们主要的活动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与支持下,组织签名运动,联合发表了各种宣言、抗议书等等。”由于《沧南行》是一本地下刊物,发行量不是太大,且可能的知情者张雪岩早在1950年1月就已去世,其他各位九三先贤很可能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刊物,久而久之,《意见》发表之事就无人知晓了。 据统计,1946年1月至1949年1月,九三学社以各种名义,共发表对国事的意见、主张、宣言或谈话20余篇。《意见》是北平和平解放前,最后一篇得以保存的以九三学社名义发表的文献,同时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篇发表在地下刊物上的文献。在此之前,九三学社的相关意见、主张、宣言或谈话,主要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上海《文汇报》《时代日报》、北平《世界日报》《新民报》等报刊上。 1947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勒令停刊,九三学社从此失去了一个发表政治主张和意见的重要平台,相关意见、主张想要见诸报端就越来越困难。1947年3月18日,许德珩曾致信在沪的九三学社创始人笪移今,特意探讨了对四外长会议意见书的发表问题。信中说:“为四国外长会议问题,此间曾讨论两次,昨日获有结果。成中西文意见书各一份,今特寄上,请转沪上社友讨论。为时间便利,西文稿已交由此间外国友人发出,中文稿交《大公》《文汇》通讯人员,惟不知能发表得出来否?”由此信可知,如何发表九三学社的意见和主张,已经成为许德珩等九三前辈较为头疼的一个问题。所幸的是,该意见书最终发表在1947年3月20日的上海《大公报》上,全文在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档案室也有留存。 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氛围下,九三学社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遂亦逐渐以幕后及地下方式进行”,有些文件就未公开发表。例如,1947年3月,针对国民党当局攻占延安,九三学社“曾警告蒋政府,认为此种狂妄行为应负内战全部责任。”8月,针对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九三学社曾提出要求美国“撤退在华驻军,并即时停止援助蒋介石的屠杀中国人民的反动战争的书面请求”。1948年3月,针对国民党当局召开第二次伪国民大会,九三学社“曾在北平发表宣言,反对伪国代。宣言油印张贴各学校”。较为可惜的是,以上3份文件的全文均未能保存下来。 在今天的八个民主党派中,九三学社公开响应“五一口号”最晚,主要就是因为九三学社始终身处国统区,不便公开发表意见。据袁翰青回忆,1948年5月,九三学社在北平的社员从广播里收听到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消息后,“大家非常兴奋,当时就请许老起草了一个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号召的代电,并由他负责发了出去。”但这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代电至今也未被找到。这一时期,为了继续推进革命工作,同时又不暴露组织,九三学社多采取发起个人联名的方式公开发表意见和主张,比如《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抗议轰炸开封》《对北平当局毒杀东北青年“七·五”惨案宣言》等。 通过对这则史料的研究学习,笔者深深感到,史料是会说话的文字,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经过长期积累,九三学社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上,取得可喜成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这项工作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空白点。就改革开放前的社史资料搜集整理来说,主要是需要在查漏补缺上下功夫,着力增强史料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而改革开放后的社史资料搜集整理,比如九三学社的履职工作和自身建设,目前还存在大片尚待开垦的园地。如何更加系统、完整、全面地搜集、整理和研究九三学社史料,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所有社史工作者来共同努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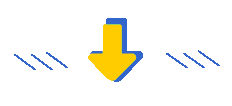

作者:乔发进 系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副主任
